我家狗叫土豆,是条金毛。
除了掉毛和吃得多,没别的毛病。
至少在我搬进这个老小区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小区什么都好,安静,租金便宜,绿化也好得不像话,大片大片的香樟树,夏天连空调都省了。
唯一的缺点,是我的邻居。
就住我对门,姓刘,一对沉默寡言的老夫妻。
问题不出在他们身上,出在土豆身上。
土豆,一条以“中央空调”闻名犬界的金毛,见到收废品的都想摇着尾巴上去跟人拜个把子。
但唯独对着邻居家,具体来说,是邻居家那面光秃秃的,和我家阳台隔着一小片草地遥遥相望的墙,它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敌意。
每天,不定时,土豆会突然从地板上弹起来,冲到阳台,对着那面墙,狂吠。
不是那种看见同类的兴奋犬吠,是低沉的、充满警告意味的、连背上金毛都一根根炸起来的咆哮。
一开始我以为是巧合。
可能墙里有老鼠,或者有什么它能闻到我闻不到的气味。
我安慰自己,老小区嘛,生态系统比较丰富。
我把土豆拉回来,给它零食,摸它的头。
“祖宗,安静点,咱们是租户,要低调。”
土豆呜咽两声,舔舔我的手,但那双黑亮的眼睛,依旧死死盯着那个方向。
没过几天,对门的刘婶在楼道里碰到我,脸上带着点为难的笑。
“小陈啊,你家狗狗……是不是有点太活泼了?”
我瞬间清楚,这是投诉来了。
我连声道歉,“对不起刘婶,我回头就教训它,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喜爱冲那边叫。”
刘婶摆摆手,人倒是很和气,“没事没事,我们年纪大了,觉轻。你白天上班,它自己在家,是不是孤单了?”
这话说得我心里更不是滋味。
我一个 freelance,在家办公,土豆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二十个小时是挂在我身上的。
孤单?它孤单个屁。
但人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只能继续点头哈腰,“是是是,我多陪陪它。”
送走刘婶,我关上门,看着蹲在门口一脸无辜的土豆,气不打一处来。
“你他妈是想让咱俩一块儿卷铺盖滚蛋吗?”
土豆歪着头,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好像在问我为什么生气。
我能为什么?
还不是由于你这个逆子。
我试过许多办法。
网上买的止吠器,挂在它脖子上,一叫就震动。结果土豆叫得更凶了,好像在控诉我虐待它。
还有人说用零食引诱,在它叫的时候,用好吃的把它引开。
这个方法一度奏效,但后果是,土豆学会了新技能——为了骗零食,它会假模假样地对着那面墙“汪”一声,然后立刻回头,满眼期待地看着我。
我的钱包和我的耐心,一起被迅速消耗。
最尴尬的一次,我正开着视频会,跟甲方爸爸汇报方案。
土豆毫无征兆地又开始了它的“每日一咆”。
那声音,通过我这廉价的麦克风,被完美地、立体地传送到了会议室里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我看到甲方老总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
“陈阳,你那边……是在拆家吗?”
我恨不得当场把土豆炖了。
那天之后,我下定决心,必须搞清楚,那面墙后面,到底他妈的有什么。
我开始观察我的邻居,刘叔。
刘婶还算正常,会出门买菜,会在楼下跟别的老太太聊天。
但刘叔,我搬来快三个月了,跟他碰面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他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工装,背很佝偻,走路几乎没有声音,像个幽灵。
最重大的是,他的眼神。
那是一种……怎么说呢,很空洞的眼神。你看向他,他也在看着你,但他的视线好像穿过了你,落在了某个虚无的地方。
每次土豆开始狂吠,如果刘叔在家,他们家的窗帘就会被悄悄拉开一条缝。
我能感觉到,有目光从那条缝里射出来,冰冷,锐利。
这让我心里有点发毛。
我开始胡思乱想。
这老头,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上那些社会新闻,什么独居老人精神失常,什么邻里矛盾激情杀人……一幕幕在我脑子里闪过。
我一个单身男青年,带着一条除了吃就是睡的狗,真要出点什么事,连个报警的人都没有。
不行,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主动出击,才是唯一的活路。
我从网上买了一个最小的、带夜视功能的家用监控。
那种伪装成充电头,插在插座上就行的。
我把它装在了阳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镜头,精准地对准了我家楼下那片小草地,以及草地对面,刘叔家那面该死的墙。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我家土豆跟疯了似的。
安装监控的第一天,风平浪静。
我像个偷窥狂,把手机投屏到电脑上,一边画图,一边盯着监控画面。
画面里,只有风吹过的树叶,偶尔路过的野猫,还有几个在草地上打滚的小孩。
土豆趴在我脚边,睡得口水流了一地。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反应过度了。
也许土豆只是单纯的……?
第二天,依旧如此。
我有点泄气了。
我甚至开始反思,我是不是对邻居有太大的恶意了?人家可能就是单纯的社恐,不爱出门。
我这又是怀疑又是装监控的,跟个变态似的。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画图画到半夜,脖子都快断了。
我伸了个懒腰,习惯性地瞥了一眼监控画面。
就是这一眼,让我浑身的血都凉了半截。
监控画面里,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人影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戴着帽子,看不清脸。
他正站在那片小草地上,手里……好像拿着一把铲子。
时间,凌晨一点半。
我瞬间睡意全无,心脏“咚咚咚”地狂跳,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是他。
虽然看不清脸,但那个佝偻的背影,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刘叔。
他想干什么?
大半夜的,拿着铲子,在我家楼下的草地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无数恐怖电影的片段闪过。
埋尸?
藏赃物?
还是……别的什么?
我死死盯着屏幕,连呼吸都忘了。
只见刘叔走到草地中央,那棵老樟树下,左右看了一眼。
我们这栋楼的构造很奇怪,这片草地正好是个视觉死角,除非从我这个角度的阳台往下看,否则很难被发现。
他选了个绝佳的位置。
然后,他开始挖。
一铲,一铲,动作很慢,但很有力。
泥土被翻开,在夜视镜头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白色。
土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身后,喉咙里发出那种我再熟悉不过的低吼。
但这一次,它没有狂吠。
它只是低吼着,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像一张拉满的弓。
我一手捂住它的嘴,另一只手紧紧攥着手机。
我该怎么办?
报警?
跟警察说什么?说我邻居半夜在我家楼下挖坑?警察会不会觉得我是个?
万一他只是在……种花呢?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自己否决了。
谁他妈会在凌晨一点半种花?
挖了大致十几分钟,一个不深不浅的坑出现了。
刘叔停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
那东西不大,像个盒子。
他把盒子放进坑里,然后开始填土。
他的动作很轻,很仔细,仿佛在安放什么稀世珍宝。
填好土,他又从旁边的草地上,小心翼翼地揭了几块草皮,严丝合缝地铺在翻开的泥土上。
做完这一切,他又直起身,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夜风吹过,吹动他花白的头发。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沉重的悲伤,像一块巨石,透过屏幕,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然后,他转身,拿着铲子,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楼道的阴影里。
一切恢复了平静。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被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下。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头疼得要命。
我几乎一夜没睡,脑子里反复播放着监控里的画面。
那个盒子。
盒子里到底是什么?
我走到阳台,往下看。
那片草地看起来和往常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绝不会信任昨晚发生的一切。
土豆又开始叫了。
但和之前不一样,它的叫声里少了几分暴躁,多了几分焦急和委屈。
它绕着阳台打转,爪子不停地扒拉着玻璃门,想出去。
“你想干嘛?”我问它。
它用头拱我的腿,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楼下。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子里成型。
我要不要……把它挖出来?
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像藤蔓一样疯长,缠得我喘不过气。
我知道这很危险,也很不道德。
这是窥探别人的隐私。
可我控制不住我的好奇心,还有那种莫名的……不安。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需要知道,我每天生活的这个地方,地下到底埋着什么。
我决定找我的发小,胖子张。
胖子是我唯一的朋友,一个体重两百斤,胆子只有二两的网文写手。
我把事情跟他一说,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一分钟。
“陈阳,”他终于开口,声音都在发抖,“你丫是不是撞鬼了?”
“我他妈要是撞鬼了就好了,”我烦躁地说,“目前是活人,一个大活人,在我家楼下埋东西。”
“你报警啊!”胖子喊道,“这还用问?”
“我怎么报?我说我偷窥邻居,发现他半夜埋东西?警察来了,一挖,要是个空盒子,或者是什么他家祖传的咸菜坛子,我他妈怎么收场?”
“那……那万一不是咸菜坛子呢?”胖子的声音更抖了,“万一是……是手指头呢?”
我被他这个比喻恶心得够呛。
“所以,我才找你商量。”
“商量个屁!你赶紧搬家!这地方邪门!”
“我刚交了半年房租。”我冷静地提醒他。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要不,”胖子小心翼翼地提议,“咱俩……晚上……去把它挖出来?”
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你说的啊。”
“我操,我就是说说而已!你别当真啊!”
“晚上十点,带上铲子,我在楼下等你。”
我没给他反悔的机会,直接挂了电话。
我知道胖子会来。
他这人,嘴上怂得要死,但真有事,他比谁都靠谱。
一个下午,我都坐立不安。
我强迫自己工作,但脑子里全是那个盒子。
我甚至开始在网上搜索,“邻居半夜埋东西怎么办”。
答案五花八门。
有人说报警,有人说直接去问,还有人说,假装不知道,不然会惹祸上身。
我关掉网页,心里更乱了。
傍晚的时候,刘婶敲了我的门。
她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饺子,热气腾腾的。
“小陈,我自己包的韭菜鸡蛋馅儿,你尝尝。”
我愣住了。
我看着她脸上和善的笑容,再想想昨晚她丈夫诡异的行为,一种巨大的荒谬感笼罩了我。
“刘婶,这……这怎么好意思。”
“客气啥,远亲不如近邻嘛。”她把碗塞到我手里,“快趁热吃。”
我端着那碗饺子,心里五味杂陈。
如果他们真的是坏人,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如果他们不是坏人,那刘叔的行为,又该怎么解释?
饺子很好吃,皮薄馅大。
但我吃得食不知味。
晚上九点五十,胖子给我发了条微信。
【我到你小区门口了,你那邻居没动静吧?】
我走到阳台,悄悄往对门看了一眼。
他们家的灯黑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没动静,睡了。】我回他。
【操,我怎么感觉跟做贼似的。】
【别废话,赶紧的。】
我从储物间翻出一把之前种花用的小铁铲,又拿了个手电筒,蹑手蹑脚地出了门。
土豆跟在我身后,我想把它关在家里,它却死活不肯,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
我怕它叫出声,惊动邻居,只好带上它。
“你给老子安分点,敢乱叫一声,回去就把你阉了。”我恶狠狠地威胁它。
它好像听懂了,呜咽了一声,夹起了尾巴。
我和胖子在楼下碰了头。
他果然带了把大铲子,还戴着个鸭舌帽,鬼鬼祟祟的。
“我操,你这阵仗,不知道的以为咱俩要去盗墓。”我吐槽他。
“差不多,”胖子压低声音,“我他妈腿都是软的。你说,万一挖出来一只手,怎么办?”
“闭上你的乌鸦嘴。”
我们俩,加上一条狗,像三个笨拙的间谍,潜伏到了那棵老樟树下。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地面。
果然,有一块地方的草皮颜色,和周围不太一样。
就是这里。
“挖吧。”我说。
胖子咽了口唾沫,握紧了铲子。
“那个……谁先来?”
我白了他一眼,接过他手里的铲子,“看你那怂样。”
我开始挖。
泥土很松软,显然是刚翻动过不久。
胖子在我旁边,用手机的手电筒给我照亮,紧张得像个望风的。
土豆蹲在一旁,一动不动,死死盯着我挖开的坑。
它的反应很奇怪。
没有低吼,也没有焦躁,就是安静地看着。
那种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危险的坑,倒像是在……等待什么。
挖了大致二十公分深,铲子“当”的一声,碰到了一个硬物。
我和胖子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紧张。
“是……是那个盒子。”胖子声音发颤。
我扔掉铲子,用手去刨。
很快,一个木制的盒子,出目前我们面前。
盒子不大,大致三十公分长,二十公分宽,看起来很旧了,边角都磨得发亮。
上面没有锁。
我把它从坑里捧出来,入手很轻。
“打开看看?”胖子凑过来,比我还好奇。
我犹豫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超出了我的控制。
打开它,就意味着我彻底侵犯了一个陌生人的秘密。
不打开,我这辈子可能都会被这个盒子折磨。
“开吧,”我咬咬牙,“都到这份上了。”
我把盒子放在草地上,深吸一口气,伸出手,慢慢地,掀开了盒盖。
我和胖子,同时把头凑了过去。
预想中的手指头、骨头、或者什么血淋淋的玩意儿,都没有出现。
盒子里,只有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一个旧得发黄的毛绒小狗玩具。
一本翻烂了的儿童画册。
几块五颜六色的积木。
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已经有些褪色了,上面是一个笑得很灿烂的小男孩,大致七八岁的样子,怀里抱着一条……金毛。
照片的背景,就是我们目前站着的这棵老樟树。
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用圆珠笔写的小字:
念念,八岁生日快乐。
我和胖子都愣住了。
“这……这是什么情况?”胖子一脸懵逼。
我没说话,只是拿起那张照片,翻了过来。
照片背后,还有一行字。
【我的念念,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字迹很娟秀,像是女人的手笔。
我突然清楚了什么。
这个盒子,不是什么罪证。
这是一个父亲,对死去的儿子,无尽的思念。
就在这时,我身后的土豆,突然“呜”地叫了一声。
那声音,和我以前听过的任何一次都不同。
不是咆哮,不是警告,也不是撒娇。
那是一种……悲伤的,带着哭腔的呜咽。
它走到那个打开的盒子旁边,低下头,用鼻子轻轻地,嗅了嗅那个毛绒小狗玩具。
然后,它伸出舌头,舔了舔照片上那个小男孩的笑脸。
月光洒在它金色的毛发上,我第一次发现,它的眼睛里,竟然蓄满了泪水。
我和胖子,彻底石化了。
我们像两个一样,站在原地,看着一条狗,对着一个装着逝去孩子遗物的盒子,流露出比人还要悲伤的表情。
“我操……”胖子喃喃自语,“这狗……成精了吧?”
我没有理他。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刘叔,刘婶,那个叫念念的孩子,这条通人性的狗……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我浑身一僵,像被电击了一样。
我和胖子,机械地,一点一点地,转过身去。
刘叔就站在我们身后不到五米的地方。
他还是穿着那身灰色的工装,手里没有拿铲子,只是静静地站着。
他的脸,隐在树影里,看不真切。
但我能感觉到,他那双空洞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们,或者说,盯着我手里的那个盒子。
完了。
我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字。
人赃并获。
胖子已经吓得快尿裤子了,他躲在我身后,一个劲地拽我衣服。
“陈阳……陈阳……快……快跑啊……”
跑?
我往哪跑?
我感觉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
我看着刘叔,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道歉?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是我,亲手挖开了他埋藏在心底最深的伤疤。
空气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胖子粗重的喘息声。
打破这份寂静的,是土豆。
它没有跑,也没有叫。
它只是叼起那个毛绒小狗玩具,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了刘叔的脚边。
然后,它把玩具放下,抬起头,用那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刘叔。
喉咙里,发出轻轻的、讨好的“呜呜”声。
刘叔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他低下头,看着脚边的土豆,和那个熟悉的玩具。
月光下,我清楚地看到,两行浑浊的泪水,从他那双空洞的眼睛里,滚落下来。
他缓缓地蹲下身,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微微颤抖的手,想要去摸土豆的头。
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
他好像在害怕什么。
土豆却主动把头凑了过去,在他的手心上,蹭了蹭。
刘叔的身体,又是一震。
他终于忍不住,一把抱住了土豆的脖子,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它温暖的、金色的毛发里。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在寂静的午夜,抱着一条素不相识的狗,发出了压抑了太久的、如同野兽哀嚎般的哭声。
我和胖子,站在一旁,彻底不知所措。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可以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绝望。
那哭声,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在我的心上。
我突然觉得,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
“对不起。”
我终于说出了话,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刘叔,对不起。”
刘叔没有理我,他只是抱着土豆,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
“念念……我的念念……”
“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没用……”
哭了很久,他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他松开土豆,用袖子胡乱地抹了一把脸,站起身。
他看着我,眼神不再空洞,也不再冰冷。
那是一种……混杂着悲伤、疲惫和一丝解脱的复杂眼神。
“进来……坐坐吧。”他说。
我和胖子,像两个被审判的罪犯,跟着刘叔,走进了那扇我们揣测了无数次的门。
刘婶被哭声惊醒了,正穿着睡衣,一脸惊慌地站在客厅里。
看到我们,她愣住了。
“老刘,这……这是怎么了?”
刘叔没有回答她,只是走到沙发旁,颓然坐下,把那个木盒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把胖子推到前面,自己则深深地鞠了一躬。
“刘叔,刘婶,对不起。我们……我们不是故意的。”
刘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丈夫怀里的盒子,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好像清楚了什么,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客厅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从土豆的狂吠,到我的怀疑,再到我装监控,以及最后,我和胖子愚蠢的“盗墓”行为。
我没有为自己辩解。
我只是一五一十地,陈述我的罪行。
我说完,客厅里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过了很久,刘婶长长地叹了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她走到饮水机旁,给我们俩倒了两杯水。
“不怪你们,”她把水杯放到我们面前,声音沙哑,“是我们……吓到你们了。”
“念念,是我们的儿子。”
刘婶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他特别喜爱狗,尤其是金毛。他说金毛笑起来,像太阳一样。”
“我们家以前也养过一条,就跟……就跟你家土豆长得差不多。”
“念念八岁那年,得了白血病。没撑过去。”
“他走的那天,正好是他九岁生日的前一天。”
刘婶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他走了后来,他爸就像变了个人。不说话,不笑,整天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那条金毛,没过多久,也跟着去了。医生说,是抑郁死的。”
“这个盒子,”她指了指刘叔怀里的木盒,“里面装的,都是念念生前最喜爱的东西。每年他生日这天,他爸都会把这个盒子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
“以前我们住平房,院子里有棵大树,是念念最喜爱玩的地方。他爸就把盒子埋在树下,他说,这样念念就不会孤单了。”
“后来拆迁,我们搬到了这里。院子没了,树也没了。”
“他爸找了很久,才发现你们家楼下那片草地,那棵树,跟我们以前院子里的那棵,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
刘婶说不下去了,捂着脸,泣不成声。
我终于清楚了。
所有的一切,都有了答案。
没有罪犯,没有阴谋。
只有一个无法走出丧子之痛的父亲,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祭奠着他逝去的孩子。
而土豆……
我回头看了一眼蹲在门口的土豆。
它为什么会对着那面墙狂吠?
是巧合吗?
还是说,它真的能感觉到什么?
是感觉到那片土地下,埋藏的属于一个同样喜爱狗的小男孩的遗物?
还是感觉到,墙那边,那个老人身上,散发出的浓得化不开的悲伤?
我不知道。
也许,狗的世界,真的有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感知。
“对不起。”我再次道歉,这次,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不该……不该去挖那个盒子。”
刘叔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红肿,但眼神却清明了许多。
“不,”他摇摇头,声音嘶哑,“也许……该谢谢你们。”
“这些年,我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以为把念念藏起来,就没人知道,他也就不会离开我。”
“我不敢跟人说,不敢哭,我怕我一哭,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今天……”他看了一眼蹲在门口的土豆,“看到它,我就想起了念念。我想起了念念抱着我们家大黄,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可以哭出来了。”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
聊那个叫念念的孩子,聊他有多机智,多调皮,多喜爱小动物。
聊那条叫大黄的金毛,聊它有多忠诚,多通人性。
刘叔和刘婶,像是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话匣子,把积压了多年的思念和痛苦,全都倾诉了出来。
我和胖子,就安静地听着。
我们像是两个闯入别人悲伤故事的局外人,却意外地,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倾听者。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离开。
临走前,刘叔叫住了我。
“小陈,”他说,“后来……能不能让土豆,多来我们家坐坐?”
我看着他眼中,那小心翼翼的期盼,用力地点了点头。
“随时欢迎。”
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土豆不再对着那面墙狂吠。
它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去对门串门。
刘婶会给它准备好吃的,刘叔会拿着梳子,一遍一遍,耐心地给它梳毛。
他们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刘叔的话也多了起来。他会跟我聊新闻,聊股票,聊年轻人喜爱的东西。
他甚至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加了我的微信,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我的朋友圈下面点赞。
我们成了真正的“邻居”。
胖子后来跟我说:“陈阳,我觉得你家土豆,不是狗,是月老。”
“是狗月老。”我纠正他。
“你说,它是不是真的能看见……那个叫念念的小孩?”胖子又问。
我没有回答。
我只是走到阳台,看着楼下那片草地。
那棵老樟树,在阳光下,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有些事情,不需要答案。
你只需要信任,在这个坚硬、冷漠的城市里,总有一些温暖的、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存在。
它们可能是一只狗的通灵,也可能是一个父亲深沉的爱。
它们连接着生与死,过去与目前,让我们在冰冷的钢筋水泥里,还能感受到一丝柔软的慰藉。
又过了一年。
到了念念生日的那天。
傍晚,刘叔敲开了我的门。
他手里没有拿那个木盒子,而是提着一袋狗粮。
“小陈,”他笑着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晚上有空吗?你刘婶包了饺子,一起来吃吧。”
“好啊。”我笑着答应。
“把土豆也带上,”他补充道,“今天……也算是它的节日。”
我愣了一下,随即清楚了他的意思。
我点点头,“好。”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条狗,围坐在一张小小的餐桌旁。
电视里放着无趣的晚会。
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
刘婶给我们每个人都夹了满满一碗饺子。
刘叔拿出一瓶藏了很久的白酒,给我,也给他自己,倒了一杯。
“小陈,”他举起杯子,“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我端起杯子,“该我谢谢你们,把我喂胖了这么多。”
我们相视一笑,一饮而尽。
土豆趴在桌子下,啃着刘叔给它买的磨牙棒,发出满足的“咔嚓”声。
一切都那么平常,又那么不平常。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的那个夜晚,我和胖fenzi,像两个一样,在楼下挖坑。
那时候,我以为邻居是恶魔,以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和恶意。
但目前我知道了。
真正的恶魔,是你内心的猜忌和冷漠。
而真正的天使,可能就是你身边,那个沉默寡言,却在用自己笨拙的方式,爱着这个世界的人。
也可能,是一条只会掉毛和吃的金毛。
它用它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叫作爱,什么叫作慈悲。
吃完饭,我陪刘叔在楼下散步。
土豆在我们前面,欢快地跑着,追逐着自己的尾巴。
我们走到那棵老樟树下。
刘叔停下脚步,抬头看着繁茂的枝叶。
“你说,”他轻声问,“念念目前,是不是也长成大小伙子了?”
“肯定是的,”我说,“必定又高又帅,跟你一样。”
刘叔笑了。
“他要是还在,肯定也喜爱土豆。”
“嗯。”
“小陈,你说人死了,到底会去哪儿?”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们不会真的离开。”
“他们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变成吹过我们脸颊的风,变成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那一部分。”
“只要我们还记得他们,他们就永远活着。”
刘叔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夜空。
过了很久,他长长地舒了口气。
“回家吧,”他说,“天凉了。”
我们往回走。
土豆跑过来,用头蹭了蹭刘叔的腿,又蹭了蹭我的。
然后,它抬起头,对着我们,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像太阳一样的笑容。
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在它的身后,站着一个同样笑得灿烂的小男孩。
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怀里抱着一个毛绒小狗玩具。
他对着我们,用力地挥了挥手。
我揉了揉眼睛。
再看时,那里只有昏黄的路灯,和随风摇曳的树影。
我笑了。
原来,你真的没走。
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们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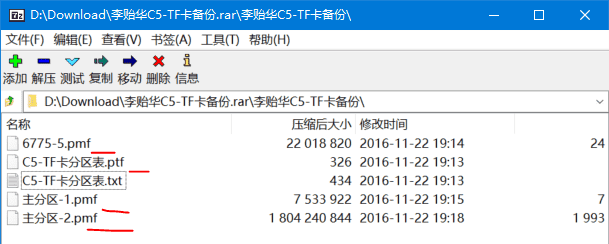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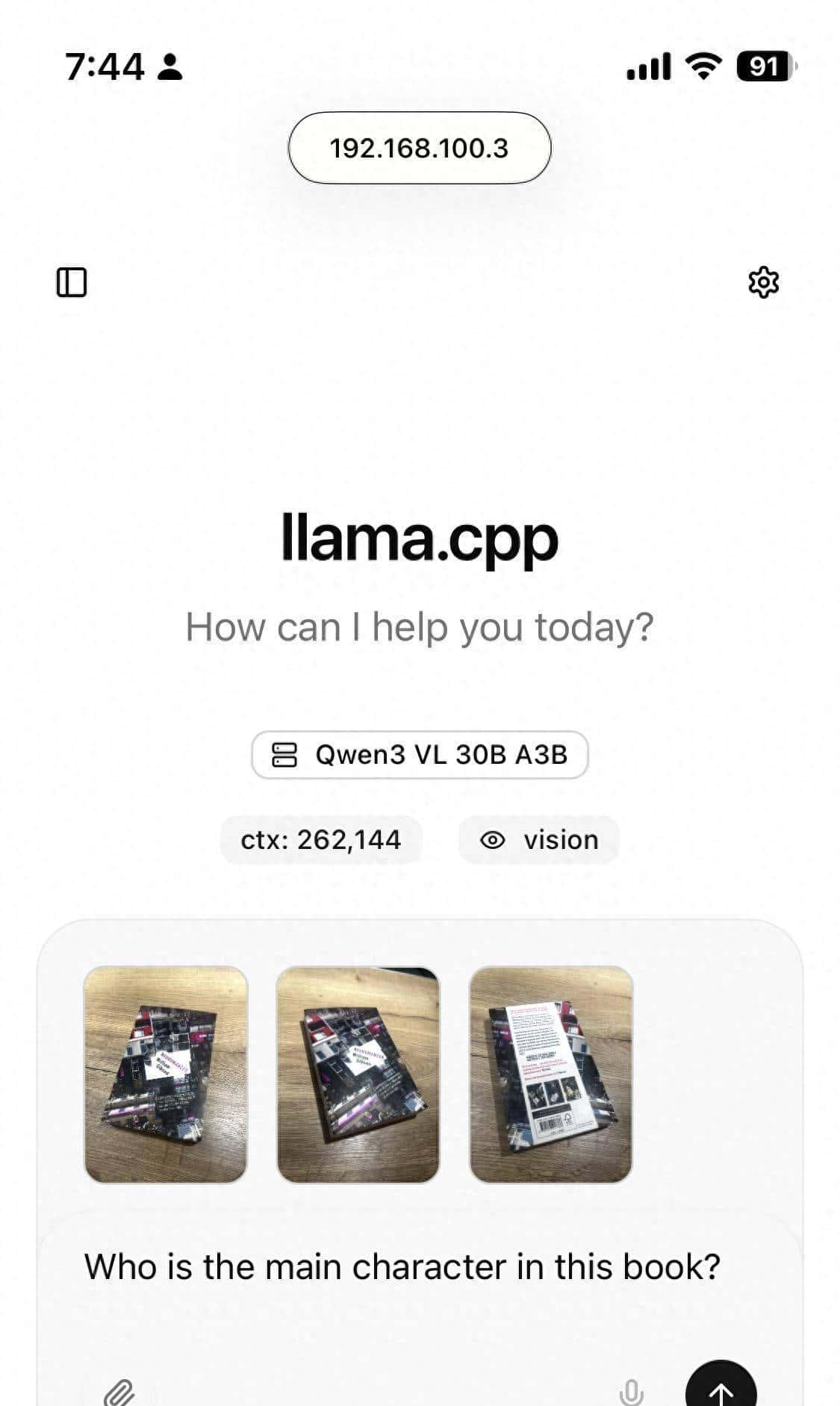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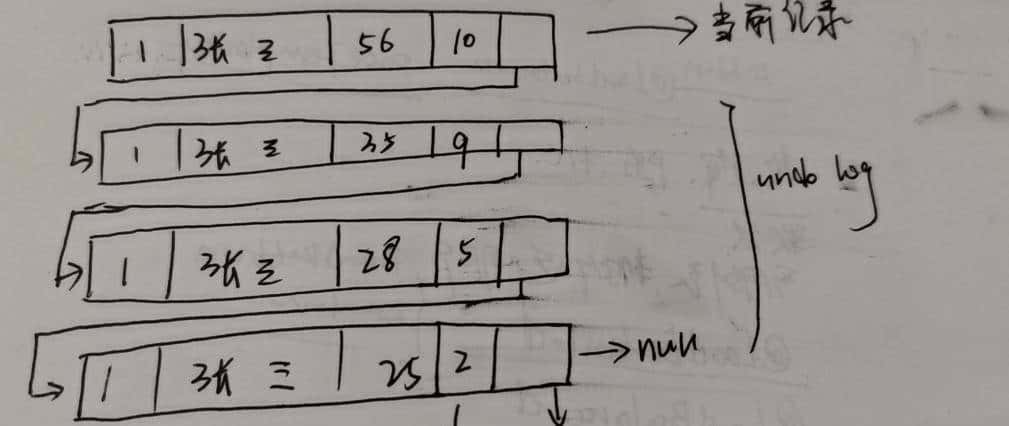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