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了一个,然后令我目瞪口呆的一幕出
1.
午夜十二点,我还在律所改最后一遍合同。
手机终于在接完第三个催命电话后,彻底黑屏。
我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摸出陈嘉生的备用机。他嫌新手机功能太繁琐,旧的这个就一直放在我办公室充电,以备不时之需。
开机,解锁,是他的生日。七年了,没变过。
屏幕亮起,界面干净得像他这个人。
我点开打车软件,准备回家。
然后,我看到了“常用同行人”那一栏。
系统默认的,根据近期高频共乘记录生成。
我自己的账号,常用同行人是我,是陈嘉生,是我妈。我们的生活轨迹高度重合,像三条缠绕的麻绳。
而陈嘉生的常用同行人列表里,第一个,不是我。
是一个备注为“小安”的人。
头像是个卡通兔子,看不出男女。
我点开那个头像,软件跳转到个人主页,一片空白。
但地址记录不会骗人。
最近一个月,他送“小安”回家的次数,是二十三次。
终点是“香樟路112号,七月公寓”。
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地址。
而他回我们自己家的次数,是七次。
窗外的雨点砸在玻璃上,噼啪作响,像有人在用鞭子抽打这个沉寂的夜晚。
办公室的白炽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光线冷得像手术台。
我的指尖有点凉。
我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作为一名执业八年的合同律师,我习惯了用证据和条款说话。
我关掉打车软件,点开了相册。
最新的照片,是一周前我们家庭聚餐时拍的。照片里,他揽着我的肩,笑得温和。他脖子上挂着他妈妈给的翡翠平安扣,贴着他的锁骨。
那块玉,据说是他家的传家宝,只传给认定的儿媳。
我盯着那块莹润的玉,忽然觉得有些刺眼。
我把手机息屏,放回抽屉,然后走到窗边。
楼下车水马龙,霓虹灯在雨幕里晕开,像一幅被打湿的浓墨重彩的油画。
我没有哭。
我只是觉得,房间里的灯泡,好像坏掉了。
它还亮着,但光线不对。
有点暗,有点晃,还带着一点危险的、即将熄灭的预兆。
2.
时间倒退两天。
那是一个周六的傍晚,我难得没有加班。
我炖了一锅莲藕排骨汤,是我们刚在一起时,他最喜爱喝的。
我们结婚七年,从一无所有到在这座城市扎下根,买了房,买了车。外人眼里,我们是奋斗伴侣的典范。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根维系着彼此的线,已经绷得有多紧。
三年前,我被诊断出输卵管堵塞,不易受孕。
我们跑遍了各大医院,吃过数不清的中药西药,做过两次试管,都失败了。
从那后来,家里的空气就变了。
不再有轻松的玩笑,连拥抱都带着一丝程式化的疲惫。
陈嘉生开始频繁地加班,他说建筑设计院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忙得像个陀螺。
我理解他。我知道他作为家里独子,背负着怎样的压力。
他妈妈每次打电话来,都会旁敲侧击地问:“小舒啊,肚子还没动静吗?要不要去庙里拜拜?”
我把汤盛好,放在餐桌上。
他回来了,带着一身的疲惫。
“回来了?洗手吃饭吧。”我说。
他点点头,把公文包放在玄关,换鞋。一系列动作,安静又熟练。
饭桌上,我们各自沉默地吃着。
“汤很好喝。”他忽然说。
“嗯,你喜爱就好。”
“最近院里又接了个大活,一个度假村的整体规划,可能要更忙了。”他解释道,像是在做一个工作汇报。
“注意身体。”我夹了一块排骨到他碗里。
他看着碗里的排骨,没有动,只是拿起汤勺,又喝了一口汤。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小舒,”他顿了顿,“有时候我觉得……很累。”
“我知道。”
“不是身体上的累,”他抬起眼,看着我,“是一种……怎么说呢,像掉进一个黑洞里,怎么都填不满。”
我的心沉了一下。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那个关于孩子的,我们之间绝口不提的黑洞。
“会好的,”我轻声说,“我们还年轻。”
他没再说话,只是低头,把那碗汤喝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他睡得很沉,背对着我。
我看着他微微起伏的肩膀,忽然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片海。
我以为是时间的海,是生活压力的海,是无法拥有一个孩子的遗憾的海。
我从来没想过,这片海里,还停着别人的船。
3.
目前,我站在办公室的窗边,那片海已经掀起了风暴,而我站在风暴中心,异常平静。
我拿起自己的手机,开机。
电量还剩百分之一。
我用这最后的电量,做了一件事。
我给我带的实习生发了条信息:帮我查一个地址,香樟路112号,七月公寓。查一下这个小区的开发商、物业信息以及近期的二手房成交均价。
然后,我点开了和陈嘉生的聊天框。
输入:“你在哪?”
发送。
手机彻底关机。
我没有叫车,而是走进了冰冷的雨夜里。
我需要吹吹风。
我需要让这场雨,把我心里那点可笑的、残存的温情,全部浇灭。
婚姻是什么?
于我而言,它是一份我们双方签字画押的终身合同。
有权利,有义务。
有共同财产,有共同债务。
最重大的条款,是忠诚。
任何一方的背叛,都是单方面违约。
而对于违约,我的职业本能告知我,第一步不是声嘶力竭地质问,而是冷静地取证、评估损失,然后选择对我最有利的解决方案。
我不是一个天生善良的女人。
我只是不喜爱把事情弄得太脏。
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和风衣,很冷。
但我的大脑,却由于这股寒意,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
我沿着马路一直走,走到地铁站。
深夜的站厅,灯火通明,空无一人。
列车从黑暗的隧道里呼啸而来,带着巨大的风声,像一头钢铁巨兽。
车厢里,光影随着列车的行进,在我的脸上明明灭滅。
像我此刻的心情。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陈嘉生的回复,发到了我的工作微信上。
“刚开完会,在和同事吃宵夜。怎么了?”
我看着那行字,没有回复。
我又点开了实习生的微信。
她效率很高,已经把资料发了过来。
“林律师,查到了。七月公寓是五年前建的,定位是‘青年白领公寓’,小户型为主。物业口碑不错,安保很严。最近的成交均价在每平八万左右。”
她还附上了一张物业公司的联系方式截图。
我看着那个均价,心里迅速计算着。
一套四十平的单身公寓,总价大致在三百万上下。
以陈嘉生的收入,他买不起。
那么,就是租的。
我继续在雨里走着。
从地铁站到家,平时十五分钟的路程,我走了一个小时。
回到家,客厅的灯亮着。
陈嘉生坐在沙发上,似乎在等我。
他见我浑身湿透,立刻站了起来,眉头紧锁:“怎么搞成这样?手机也关机,吓死我了。”
他走过来,想拿毛巾帮我擦头发。
我后退了一步。
他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空气,在那一刻,凝固了。
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怎么了?”他问,声音有些干涩。
我没有回答他。
我走到他面前,把我的手机放在茶几上,然后拿出他的备用机,点亮屏幕,打开那个打车软件。
我把手机递到他面前。
“小安,是谁?”
我问得很平静,像在法庭上询问一个证人。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
他没有看手机,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他的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客厅里,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脏上。
“我再问一遍,”我说,加重了语气,“这个常用同行人,‘小安’,是谁?”
他终于垂下眼,视线落在那块小小的屏幕上。
那个卡通兔子头像,此刻像一个巨大的嘲讽。
“一个……同事。”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颤抖。
“哪个同事,需要你一个月送二十三次?”我追问。
“她刚来,住得远,一个人不安全。”他辩解着,但毫无底气。
“是吗?”我冷笑一声,“香樟路112号,七月公寓。离我们公司,比我们家还近。陈嘉生,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还是在侮辱我作为律师的专业?”
他彻底不说话了。
他只是站在那里,高大的身躯,此刻却显得有些佝偻。
肩线垮了下来,像一座即将崩塌的山。
“我给你一个机会,”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把她约出来。我们三个人,一起谈谈。”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全是震惊和抗拒。
“小舒,你这是干什么?别把事情闹大……”
“闹大?”我打断他,“事情是你做的,不是我闹的。我只是在清理垃圾。我这个人,有洁癖。”
“这不是垃圾,这是……这是……”他语无伦次。
“是什么?”我逼近一步,“是你的爱情?是你的慰藉?是你逃避现实的港湾?”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插进我们之间虚伪的和平里。
“陈嘉生,我没有兴趣听你的故事,也没有兴趣看你表演深情。我只给你两个选择。”
“一,明天,我们三个人,坐下来,把这件事摊开说清楚。然后,我们谈离婚的财产分割。”
“二,明天,我们三个人,坐下来,把这件事摊开说清楚。然后,你和她断干净,我们签一份婚内财产协议,明确你作为过错方的责任和义务。”
我看着他瞬间失去血色的脸,心里没有一丝快感,只有一片荒芜的冷。
“你选。”我说。
4.
第二天下午三点,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我提前到了,选了一个靠窗的角落。
窗外,雨已经停了,但天空依旧阴沉。
陈嘉生带着那个叫“小安”的女孩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搅动杯子里的咖啡。
女孩很年轻,大致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素面朝天,头发扎成一个马尾,看上去干净又无辜。
她的眼睛很大,看到我的时候,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她下意识地往陈嘉生身后躲了躲。
陈嘉生的脸色很难看,他拉开我對面的椅子,示意女孩坐下。
他自己则坐在了女孩和我中间的位置,像一道尴尬的屏障。
“林……林律师。”女孩怯生生地开口,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我猜,陈嘉生已经跟她交代了我的职业。
我抬起眼,目光越过陈嘉生,落在她脸上。
“你叫安然?”我问。
她点点头。
“安然,”我放下咖啡勺,身体微微前倾,“我今天约你来,不是为了吵架,也不是为了羞辱你。我只是想告知你一些实际。”
我顿了顿,确保她正在认真听。
“第一,我和陈嘉生,结婚七年。我们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
“第二,我们目前住的房子,开的车子,以及我们所有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都属于婚内共同财产。这是法律定义,不是我个人见解。”
“第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负有忠诚义务。任何一方与婚外第三方发生超出正常社交范围的关系,都构成对忠诚义务的违背,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我每说一条,安然的脸色就白一分。
陈嘉生坐在旁边,如坐针毡,几次想开口,都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我不是在给你上法律课,”我看着安然的眼睛,语气缓和了一些,“我只是想让你清楚,你目前所处的位置,超级尴尬,也超级危险。”
“你以为你得到的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庇护和爱情,但实际上,你什么都得不到。他给不了你名分,给不了你未来。他给你租的房子,花的每一分钱,都属于我们的共同财产。严格来说,我有权向你追讨。”
安然的嘴唇开始发白,身体微微颤抖。
“我……我不知道……”她喃喃地说,“他说你们感情不好,他说你们快要离婚了……”
我笑了。
“这是所有出轨男人的标准说辞。安然,你今年二十三岁,大学刚毕业,前途一片光明。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个有妇之夫绑在一起?”
“他对我很好,”她抬起头,眼睛里泛起了水光,“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会给我买热奶茶,会在我加班的时候陪着我。在他身边,我很有安全感。”
“安全感?”我重复着这个词,觉得有些讽刺,“一个背叛自己妻子的男人,能给你什么安全感?他今天能为了你背叛我,明天就能为了别人背叛你。”
“我不是在指责你,”我放轻了声音,“我只是觉得,你值得更好的。一个清清白白,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男人。而不是像目前这样,活在阴影里,分享一个不属于你的丈夫。”
安然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默默地流泪,肩膀一耸一耸的。
陈嘉生终于忍不住了,他递了一张纸巾过去,低声说:“别哭了。”
我冷冷地看着他这个动作。
然后,我从包里拿出两份文件,放在桌上。
一份,是《离婚协议书》。
另一份,是《婚内财产协议》。
“陈嘉生,”我叫他的名字,“目前,当着安小姐的面,你来做选择。”
我把两份文件推到他面前。
“如果你选择她,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房子归我,车子归你,存款一人一半。你净身出户,去追求你的‘安全感’。”
“如果你选择这个家,那么,你就签下这份婚内财产协议。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第一,你个人名下所有财产,包括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百分之七十划归我个人所有,作为你此次过错行为的补偿。”
“第二,未来婚姻存续期间,你若再次违反忠诚义务,你将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净身出户。”
“第三,你的手机、微信、银行账户,必须对我保持完全透明。我们需要共享位置,共享密码。”
“第四,你必须立刻、马上,和安小姐断绝一切联系。包括电话、微信、以及工作上的非必要往来。”
我看着他,也看着安然。
“我这个人,不喜爱拖泥带airs。今天,就在这里,给我们三个人一个了断。”
咖啡馆里很安静,只有背景音乐在轻轻流淌。
安然停止了哭泣,她震惊地看着桌上的协议,又看看我,再看看陈嘉生。
她眼里的那种“明亮”,正在一点点熄灭。
陈嘉生的手,在抖。
他拿起那份《婚内财产协议》,一页一页地翻看。
那是我昨晚熬夜起草的,每一个条款都精准、严苛,不留任何模糊地带。
这不仅仅是一份协议。
这是我为我们的婚姻,重新设置的防火墙。
也是我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终于,他抬起头,看向安然。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挣扎、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权衡利弊后的决绝。
“对不起,安然。”他说。
然后,他拿起笔,在那份苛刻得近乎羞辱的《婚内财产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字迹潦草,力透纸背。
安然看着他落笔,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
她没有再哭,也没有闹。
她只是站起身,对我鞠了一躬。
“对不起,林律师。”
然后,她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咖啡馆。
从始至终,她都没有再看陈嘉生一眼。
那个年轻的、明亮的女孩,带着她破碎的“安全感”,消失在了阴沉的街角。
而我,看着那份签好字的协议,心里没有胜利的喜悦。
只有一种把柠檬硬生生挤出柠檬水的,酸涩的疲惫。
5.
回到家,我们之间是更深更冷的沉默。
陈嘉生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木偶,把自己摔在沙发里,一动不动。
我把那份协议收好,放进保险箱。
然后,我开始收拾安然留在我们生活里的痕迹。
陈嘉生车里那瓶她喜爱的香水。
他书房里那本她推荐的诗集。
他钱包夹层里一张小小的、她画的卡通简笔画。
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找出来,装进一个纸箱。
整个过程,我没有说一句话。
他也没有。
他只是看着我,眼神像一潭死水。
直到我把那个纸箱封好,准备拿到楼下扔掉。
他才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小舒,我们能……谈谈吗?”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
“你想谈什么?”
“我……”他似乎不知道从何说起,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抓着,“我知道我错了,错得离谱。”
“我不是想为自己辩解。我只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我把纸箱放在门口,走到他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
“你说。”我给了他一个机会,也给了我自己一个答案。
“从我们决定要做试管开始,一切就都变了。”他低着头,声音很闷。
“你每次去医院,打针、吃药、取卵……你承受着身体的痛苦,我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妈的电话,亲戚的眼神,同事的关心……所有的一切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失败的丈夫,一个不完整的男人。”
“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我们不说,但那个‘黑洞’就在那里,越来越大。我每天下班,站在楼下,都不想上来。我怕看到你失望的眼神,也怕看到我自己无能为力的样子。”
“安然……她就像……你知道吗,就像在一个很黑很长的山洞里走了很久,突然看到的一点光。”
“她年轻,有活力,看我的眼神里全是崇拜。在她面前,我不是那个生不出孩子的失败者,我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陈工’。那种感觉,让我上瘾。”
“我承认我懦弱,我可耻。我用她来逃避现实,我享受着她的崇拜,来填补我的自卑。”
“但我从来,从来没想过要和你离婚。”他抬起头,眼睛红了,“这个家,是我和你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我怎么可能不要?”
我静静地听着。
没有愤怒,也没有心软。
他的痛苦,我能理解。
但这并不能成为他背叛的理由。
“陈嘉生,”我说,“你把生活当成了一道证明题,你想向所有人证明你很成功。事业上,你做到了。但传宗接代这件事上,你失败了。所以你急于寻找另一个出口,来证明你作为男性的魅力。”
“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也在那个黑洞里。”
我的声音很平静,却让他浑身一震。
“我打的每一针,吃的每一颗药,做的每一次检查,我的身体都在告知我,我是一个有缺陷的女人。你妈妈的每一个电话,都像在我心上扎一刀。我加班,不是由于我热爱工作,是由于我不敢回家。我怕面对你的沉默,怕面对这个空荡荡的房子。”
“你找到了你的‘光’,那我呢?我的光在哪里?”
他看着我,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婚姻不是避难所,陈嘉生。它更像一个合伙企业。遇到困难,我们应该一起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某一个股东,私自挪用公款,去外面寻找慰藉。”
“我之所以没有选择离婚,不是由于我还爱你爱到无法自拔。”
我看着他的眼睛,让他看清楚我此刻的真实想法。
“是由于我们这家‘公司’,投入了太多的沉没成本。七年的时间,七年的青春,我们共同打拼下的一切……我不甘心,就这么拱手让人。”
“那份协议,不是对你的惩罚,是对我们这段关系的风险管控。从今天起,我们的婚姻,不再仅仅依靠感情维系。它有了条款,有了规则,有了违约责任。”
“感情是会变的,但白纸黑字的合同,不会。”
“所以,收起你的痛苦和眼泪。克制不是恩赐,是你的义务。忠诚不是选择,是你的责任。”
“如果你还想继续做这个家的‘股东’,就拿出你的诚意来。不是用嘴说,是用行动做。”
我说完,站起身,拿起门口的纸箱,走了出去。
当我把那个箱子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也扔掉了心里某个柔软的部分。
那个曾经信任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的,年轻的林舒。
她死了。
活下来的是一个,只信任条款和证据的,林律师。
6.
规则落地,需要可观察的证据。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契约化”的运行模式。
陈嘉生严格遵守着协议上的每一条。
他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发信息报备。
“老婆,我下班了,目前去地铁站。”
附带一张实时定位的截图。
他把所有银行卡的密码都改成了我的生日,并且开通了每一笔消费的短信通知。
我的手机,每天都会收到十几条消费提醒。
“您尾号xxxx的储蓄卡账户x月x日xx:xx支出15.00元(食堂午餐)……”
“您尾号xxxx的信用卡账户x月x日xx:xx支出32.00元(公司楼下便利店)……”
琐碎,但透明。
我们共享了手机云相册,他拍的每一张照片,我都能第一时间看到。
大部分是建筑工地的照片,还有一些设计院的日常。
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女人的身影。
他开始准时回家。
晚上七点,他会准时出目前门口,手里提着菜。
他开始学着做饭。
一开始手忙脚乱,切到手是常有的事。
厨房被他搞得像战场。
我没有帮忙,也没有嘲笑。
我只是坐在客厅,看着他一个人在厨房里,笨拙地和锅碗瓢盆作斗sem。
像一个正在努力弥补过失的实习生。
第一个星期,他做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
我们俩默默地吃完,然后他默默地去洗碗。
第二个星期,他做的番茄炒蛋,终于能吃了。
那天,他盛了一大勺到我碗里,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尝尝,今天的盐,我用小勺量的。”
我吃了一口。
味道很普通,甚至不如外卖。
“还行。”我说。
他明显松了一口气,嘴角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
我们之间的交流,依然很少。
但那种冰冷到窒息的氛围,在一点点融化。
像冰封的河面,裂开了一丝缝隙。
有一次,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
打开门,发现他没有睡,在客厅等我。
茶几上放着一碗温热的石榴银耳羹。
“看你最近咳嗽,给你炖的。”他说。
我看着那碗红白相间的甜品,在暖黄的灯光下,散发着柔和的光。
我没有说话,只是坐下来,一勺一勺地喝掉了。
味道很好。
那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没有再背对着我。
而是转向了我这边。
我们之间依然隔着一段距离,但那片曾经波涛汹涌的海,似乎正在慢慢退潮。
一个月后,他妈妈又打来电话。
还是老生常谈地催生。
以前,他总是沉默,或者敷衍地“嗯”两声。
但这一次,他很认真地对他妈妈说:
“妈,孩子的事情,我们顺其自然。小舒的身体最重大,我不想再让她受罪了。后来,您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似乎被轻轻触动了一下。
他挂了电话,看到我,有些不自然地解释:“我就是觉得……我们不能再被这件事绑架了。”
我点点头:“你说得对。”
生活像一架精密的仪器,在新的规则下,重新开始运转。
我们把时间当成一枚一枚的硬币,小心翼翼地投入,尝试换取一点点靠近。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修复。
我只知道,那个坏掉的灯泡,虽然还有裂痕,但至少,它还在努力地发着光。
7.
转眼,秋天到了。
天气转凉,我给他找出了去年买的羊毛衫。
他在穿的时候,脖子上的那块翡翠平安扣露了出来。
我伸手,很自然地帮他理了理。
我的指尖,无意中触碰到了那块玉。
冰凉,温润。
他身体僵了一下。
这是那件事之后,我们之间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肢体接触。
“这块玉,你一直戴着。”我说。
“嗯,”他低声说,“妈给的。”
“她说,是给儿媳妇的。”我看着他。
他的眼神闪躲了一下,然后又坚定地迎上我的目光。
“是。它是你的。”他说。
我收回手,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是周末,天气很好。
他说想去郊外的湿地公园走走。
我同意了。
我们像许多普通夫妻一样,在公园里散步,看芦苇在风中摇曳。
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
阳光下,我的笑容,似乎也比以前真实了一些。
回来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水果摊。
他下车,买了一大袋石榴。
“你不是喜爱吃石榴吗?”他说。
我的确 喜爱。
但我已经很久没吃过了,由于剥石榴很麻烦。
回到家,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看电视或者玩手机。
他坐在沙发上,拿出一个石榴,开始笨拙地剥。
石榴汁溅得到处都是,他的手指被染得通红。
他剥了很久,才剥出小半碗晶莹剔透的石榴籽。
他把碗推到我面前。
“吃吧。”
我看着那碗石榴,红得像一颗一颗的红宝石。
也像一颗一颗,用心捧出的真心。
我的眼眶,忽然有点热。
这是那件事之后,我第一次有了想哭的冲动。
我拿起勺子,吃了一颗。
很甜。
“陈嘉生,”我叫他。
“嗯?”
“那份协议,你想不想……修改一下?”我问。
他愣住了,看着我,似乎不清楚我的意思。
“财产那条,”我说,“百分之七十,太多了。我们可以改成……如果再有下次,百分之百。”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瞬间亮了起来。
不是那种虚假的、逃避现实的光。
而是一种,从废墟里重新燃起的,带着希望和珍视的光。
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心,很热,很干燥。
带着一股石榴的清香。
“小舒,”他声音哽咽,“谢谢你。”
我反手握住他。
“别谢我,”我说,“这是你应得的。你用你的行动,为你自己赢回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我们相视一笑。
好像,我们这家濒临破产的“公司”,终于拿到了新一轮的融资。
虽然估值大跌,但好在,还没有退市。
8.
生活似乎真的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契约化婚姻”,在严格的规则之下,竟然慢慢滋生出了一点久违的温情。
我甚至开始觉得,或许,我们可以试着把那些条款,一点一点地,内化成我们之间的默契。
直到那个周五的晚上。
我们并排躺在床上,各自看书。
这是我们最近养成的新习惯。
十一点,我准备睡了。
他放下书,也很自然地关掉了他那边的床头灯。
房间陷入黑暗和安静。
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他放在我们中间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
是来了一条新信息。
在黑暗中,那一行白色的预览文字,清晰得刺眼。
不是安然。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信息很短,只有一句话。
“陈哥,你脖子上的那个平安扣,真的是A货吗?我有点不信。”
我的睡意,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猛地睁开眼,扭头看向身边已经睡熟的陈嘉生。
他的呼吸均匀,侧脸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光里,显得安详又无害。
翡翠平安扣……A货?
那块他妈妈给的,说是传家宝的玉。
那块他信誓旦旦说“它是你的”玉。
一个全新的,我从未设想过的疑点,像一根毒刺,猝不及防地扎进了我刚刚开始愈合的心脏。
发信人是谁?
为什么会和他讨论平安扣的真假?
如果玉是假的,那真的在哪里?
或者说,从一开始,这一切就是一个谎言?
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冰冷的雨夜。
那个我以为已经被我修好的灯泡,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似乎又出现了一道新的裂痕。
而这一次,漏出来的,是比背叛本身,更让我心惊的,关于欺骗和秘密的,更深邃的黑暗。
我没有动。
我只是静静地躺着,在黑暗中,看着那个男人的睡脸。
我知道,我们之间这场关于信任和忠诚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幕,才刚刚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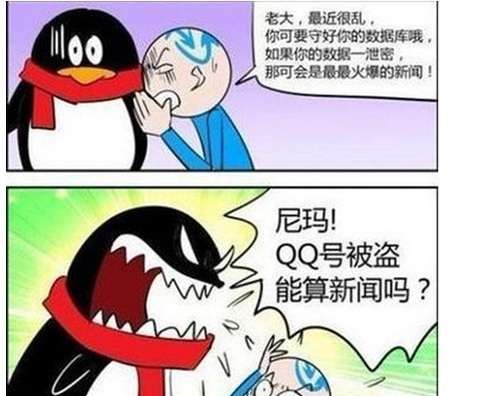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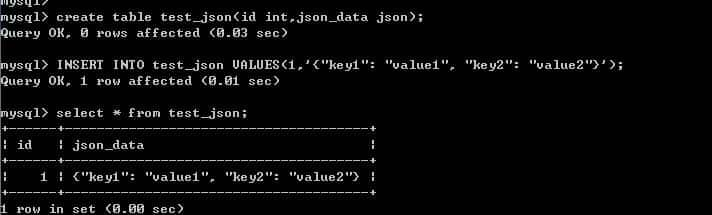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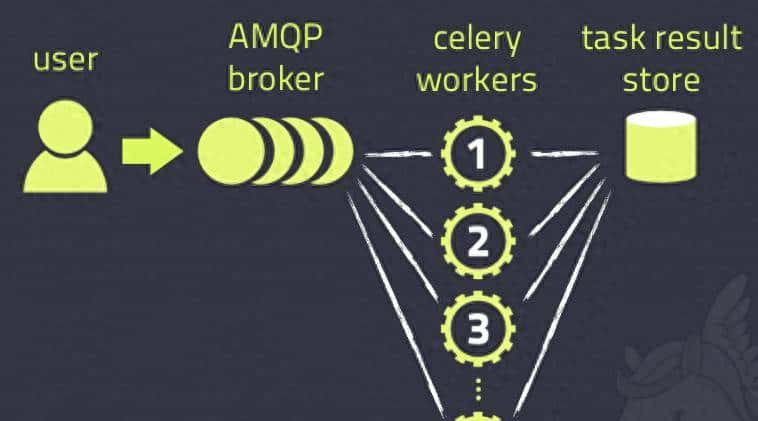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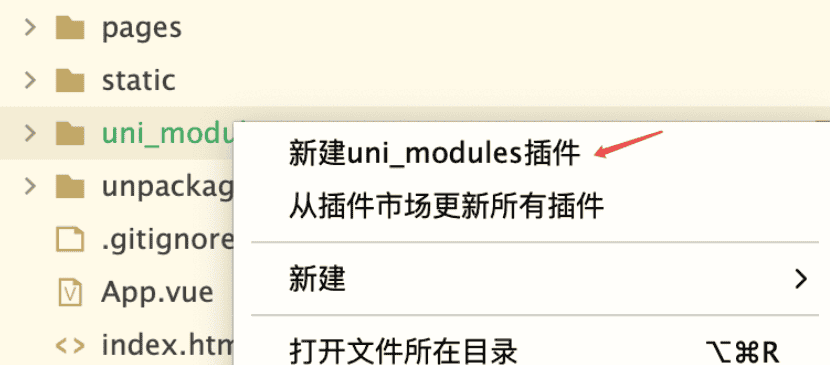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