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江城,夏天来得像个不讲理的债主,又凶又急。
太阳把柏油路晒得发软,能粘掉人半拉鞋底。
我叫陈进,二十二岁,在城东的“前进废品回收站”收破烂。
说得好听点,是“再生资源从业者”。
说难听点,就是个收破烂的。
这天下午,日头毒得能把人烤出油。我蹬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车后架上捆着两个硕大的蛇皮口袋,晃晃悠悠地往回骑。
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我眯着眼,看见回收站门口,老拐正蹲在磅秤边上,一口一口地嘬着他那个两块钱一包的“阿诗玛”。
烟雾缭绕,把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熏得像块老腊肉。
“回来了?”他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嗯。”我把车梯子一踹,从车上跳下来,感觉裤裆里都湿透了。
“今天收成怎么样?”
“别提了。”我解开绳子,把两个口袋拖下来,“就几斤烂铜,还有一堆报纸,不够今天的烟钱。”
老拐嘿嘿一笑,露出满口黄牙。
“你小子就是心气高,还想天天收到金元宝?”
我懒得理他,把蛇皮口袋里的东西倒在地上,一股子旧纸发霉和金属生锈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
老拐是回收站的老人了,一条腿年轻时在厂里被机器轧了,有点瘸,所以人称“老拐”。他看人的眼神,总像是能穿透你的皮肉,看到你兜里还剩几毛钱。
“哟,这还有个好东西。”老拐用脚尖踢了踢一堆废铁里的一个黑疙瘩。
那是个老式的保险柜,也就半米高,铁皮都锈穿了,上面贴着一张封条,写着“江城大学物理系资料室封”。
“一个破柜子,锁都坏了,里面空的。”我没好气地说,“一个退休老教授家里清出来的,当废铁卖我的,给了我十块钱。”
“教授家的东西?”老拐眼睛亮了一下,“那可得好好捣鼓捣鼓,文化人用的玩意儿,说不定夹层里有民国的地契呢。”
我嗤笑一声。
“你小说看多了吧。”
话是这么说,但我还是捡起一把锤子,对着那锈死的柜门哐哐就是几下。
“当心点,别把里面的宝贝震坏了。”老拐在一旁说风凉话。
我懒得理他,手上加了劲。
几锤子下去,柜门“咣当”一声,掉了一半。
一股更浓重的陈年旧气涌了出来,呛得我直咳嗽。
里面的确 是空的,只有一些碎纸屑和灰尘。
“看吧,我就说。”我把锤子一扔,准备把它踹到废铁堆里去。
“等等。”老拐突然凑了过来,眯着眼往里瞧。
“干嘛?”
他没说话,伸手进去摸索了一阵,然后脸色一变。
“小进,你过来。”
他的声音有点发紧。
我心里咯噔一下,也凑过去。
只见老拐从保险柜最里面的夹层里,或者说,是柜子底板和外壳之间的一个空隙里,拖出来一个东西。
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方形物件。
油布外面还用麻绳捆得死死的。
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快了起来。
“这……这是啥?”
“我哪知道。”老拐把那东西放在地上,眼神里满是贪婪和好奇,“看着像个宝贝。”
他从腰间摸出那把用了十几年的多功能小刀,小心翼翼地割开麻绳。
油布一层层打开。
露出来的,是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最普通的那种牛皮纸袋,但在1992年,这种袋子一般意味着“单位”和“正式”。
袋子没有封口,只是用棉线绕了几圈。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老拐比我更不堪,他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伸手就要去解那棉线。
“等等!”我一把按住他的手。
“干嘛?”老拐不耐烦地瞪着我。
“我……我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东西有点邪乎。
我深吸一口气,手指有些颤抖地解开棉线。
然后,我把牛皮纸袋倒了过来。
一沓厚厚的、至少有两百页的文件,滑了出来。
文件的第一页,是几个触目惊心的红色大字,印刷体,宋体加粗。
“绝密”。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长期保密”。
右上角,是一个鲜红的印章,刻着一圈五角星,中间是两个字:国防。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一万只苍蝇同时撞了一下。
空白。
一片空白。
我整个人都傻了。
老拐也傻了,他嘴里的半截烟掉在地上,火星子烫到了他的脚背,他都没反应。
“我……我操……”他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两个字。
我的手像被烫了一样,猛地把那份文件扔在地上。
仿佛那不是纸,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
“这……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我的声音都在抖。
老拐蹲下去,想捡,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像是怕被电到。
“绝密……国防……”他喃喃自语,“小进,咱们……咱们好像摊上大事了。”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那份静静躺在尘土里的文件,感觉天旋地转。
199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好几年,人们都在忙着下海,忙着赚钱,忙着“向钱看”。
国家,国防,绝密……这些词,离我们这种在社会底层刨食吃的小人物,太遥远了。
遥远得就像报纸上的新闻联播,你知道它存在,但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一毛钱关系。
可目前,它就这么赤裸裸地、不讲道理地砸在了我的脸上。
“怎么办?”我六神无主地看着老拐。
在这一刻,这个比我爹大不了几岁的瘸子,是我唯一能指望的人。
老拐的脸色比地上的废纸还白,他捡起那根烟屁股,又点上,猛吸了一口,像是要从尼古丁里汲取一点勇气。
“别慌。”他声音干涩,“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他围着那份文件,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一样,一瘸一拐地来回踱步。
我也从地上爬起来,脑子里一团乱麻。
报警?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报警。
可转念一想,怎么说?说我收破烂收到的?
警察信吗?
他们会不会觉得是我偷的?
这年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太多了。万一被当成特务抓起来,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我一个收破烂的,家里没权没势,进去了,连个能捞我的人都没有。
一想到这,我打了个寒颤。
“烧了!”我咬着牙说。
这是第二个念头,也是最直接的念头。
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就当这事从来没发生过。
老拐停下脚步,看着我,眼神复杂。
“烧了?”他反问,“你敢烧?这上面写的可是‘绝密’!万一……万一这里面的东西,关系到国家大事呢?你烧了,就是罪人。”
我被他问住了。
是啊,我敢烧吗?
我虽然是个收破烂的,但我从小受的教育,看过的电影,都在告知我,这东西不能烧。
烧了,我良心不安。
“那你说怎么办!”我几乎是吼了出来,一半是恐惧,一半是烦躁。
“要不……卖了?”老拐突然压低了声音,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危险的光芒。
我愣住了。
“卖给谁?”
“谁要,就卖给谁。”老拐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你想想,‘绝密’啊,这得值多少钱?说不定……说不定能换一栋楼!”
他的话像一个魔鬼,在我耳边低语。
钱。
我太需要钱了。
我不想一辈子收破烂,不想一辈子住在那间不到十平米、夏天漏雨冬天漏风的出租屋里。
我想穿上干净的衣服,想去“新华书店”里给晓梅买她最喜爱的那套精装版《红楼梦》,而不是每次都只能在门口看着。
晓梅是我的女朋友,在街道图书馆当管理员,人长得干净,说话也文气。
她总说我机智,不该一辈子收破烂。
可我除了收破烂,又能干什么呢?
如果……如果有了这笔钱……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但另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尖叫:不行!这是犯法!这是卖国!
我看着老拐那张由于贪婪而有些扭曲的脸,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东西不能卖!”
老拐愣了一下,随即冷笑起来。
“不卖?那你留着当传家宝啊?陈进,我告知你,这玩意儿就是个烫手的山芋,要么赶紧扔了,要么就赶紧换成钱!留在手里,早晚是个死!”
“我……”我语塞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这东西,留在手里,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我俩大眼瞪小眼,在废品站的院子里,对着一份能决定国家命运的文件,陷入了死寂。
太阳慢慢西斜,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最后,我一咬牙,把那份文件重新捡起来。
纸张的触感冰凉,却烫得我手心发麻。
“我先收起来,让我想想。”我说。
老拐没再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失望,有嘲讽,还有一丝……我说不清的担忧。
我把文件塞进牛皮纸袋,然后用油布重新包好,塞进了我那个装杂物的工具箱里,上了锁。
那个下午,剩下的活我都没心思干了。
我脑子里全是那两个红色的字:“绝密”。
晚上,我躺在出租屋那张吱吱作响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工具箱就放在床底下。
我感觉自己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一个火山口上。
我一遍遍地想,这东西到底是怎么流出来的?
那个退休的物理教授,他知道这东西在他家吗?
他是谁?
一个巨大的谜团,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了废品站。
老拐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想好了?”他问。
我摇摇头。
“小进,听我一句劝。”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事,你兜不住。要么,找个没人的地方,挖个坑埋了,烂在地下,谁也不知道。要么,你就狠下心……”
他做了个数钱的动作。
我没理他,蹬上车就往外走。
“你去哪?”
“收东西。”
我没说实话。
我根本没心情收东西。
我骑着车,漫无目的地在江城的街头乱晃。
我骑到了江城大学的门口。
看着那块写着“江城大学”四个烫金大字的牌匾,我心里五味杂陈。
当年,我也曾梦想过走进这所大学。
可惜,高考那年,我发高烧,差了几分,名落孙山。
家里穷,没钱让我复读,我就这么成了个社会青年,最后沦落到收破烂。
我把车停在路边,像个贼一样,在学校门口徘徊。
我在想,要不要进去找那个物理系的退休教授。
可我连他叫什么,住在哪都不知道。
贸然进去,怎么找?
就算找到了,我该怎么问?
“喂,大爷,你是不是丢了份国家绝密文件?”
人家不把我当才怪。
我在大学门口站了快一个小时,最后还是垂头丧气地骑车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魂不守舍。
收破烂的时候,总是走神,好几次差点被车撞了。
晚上,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惊醒。
我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监视我。
路边停着的每一辆黑色轿车,都让我心惊肉跳。
每一个看我超过两眼的陌生人,都让我觉得他是便衣。
我快被自己逼疯了。
晓梅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那天晚上,她来我出租屋给我送她织的毛衣。
江城的秋天快到了。
“陈进,你这几天怎么了?脸色这么差?”她担忧地看着我。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没事,就是有点累。”
“你是不是有心事?”她把毛衣放在床上,坐到我身边,“有事就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看着她清澈的眼睛,我差点就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了。
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我不能把她牵扯进来。
这件事,太危险了。
“真没事。”我摸了摸她的头,“就是生意不好做,愁的。”
晓梅叹了口气。
“别太累了。要不……别干这个了,我托我爸给你在图书馆找个活,虽然钱不多,但好歹是个正经工作。”
我心里一暖,又有点酸涩。
“再说吧。”
我把她送走,回到屋里,看着那件崭新的毛-衣,心里更乱了。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必须做出决定。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工具箱里的那个油布包拿了出来。
我决定,再看一次。
这一次,我要看清楚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如果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我就把它烧了。
如果……如果真的很重大,那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得把它交到该交的人手里。
我反锁上门,拉上窗帘,点亮了那盏15瓦的灯泡。
昏黄的灯光下,我再次打开了那个牛皮纸袋。
我深吸一口气,翻开了第一页。
文件的标题是:《关于“曙光”工程高超音速飞行器发动机关键技术的可行性报告》。
“曙光”工程?
高超音速飞行器?
这些词,我一个都看不懂。
但我能感觉到,这每一个字背后,都沉甸甸的。
我继续往下翻。
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图纸、数据分析。
什么“超燃冲压发动机”、“热防护材料”、“空气动力学模型”……
我像是在看天书。
但我看得出来,这是一份极其详尽、极其专业的技术报告。
我翻到文件的最后,看到了几个签名。
为首的一个名字,笔锋苍劲有力:陆承远。
后面还有几个名字,我不认识。
陆承远……
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我使劲地想,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
突然,我想起来了!
几年前,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我们国家一些功勋科学家的事迹。
其中,就有一个叫陆承远的老院士,是航空航天领域的泰斗!
纪录片里说,他为了国家的科研事业,隐姓埋名几十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难道说……这份文件,就是他的?
那他为什么会退休?文件又为什么会从一个江城大学的物理教授家里流出来?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我把文件重新装好,冷汗已经湿透了我的背心。
我意识到,我手里的,可能不是烫手的山芋。
而是这个国家的命脉。
我不能再犹豫了。
我必须找到陆承远院士,把文件亲手交给他。
可问题是,上哪去找一个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国宝级科学家?
我连他是男是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江城大学的物理系退休教授。
第二天,我下定决心,再去一次江城大学。
这一次,我不能再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我去了晓梅工作的街道图书馆。
“晓梅,帮我个忙。”
“怎么了?”
“我想查点东西。”
我没敢说实话,只说我想查一个江城大学的老教授。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我摇摇头。
“只知道是物理系的,最近刚退休。”
“这就有点难办了。”晓梅皱起了眉头,“大学里退休的教授多了去了。”
“你帮我想想办法,这对我……很重大。”我恳求地看着她。
晓梅看我一脸严肃,不像开玩笑,便点了点头。
“好吧,我试试。我们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有合作,我可以打电话问问。”
我在图书馆坐立不安地等了一个下午。
快下班的时候,晓梅才一脸疲惫地走过来。
“查到了。”她说,“物理系最近退休的教授有好几个,但我问了几个特征,列如住的老家属楼,最近在清理旧东西……符合条件的,应该是一个叫方文博的老教授。”
“方文博?”
“对。他爱人前年去世了,儿女都在国外,他一个人住,身体也不太好,前段时间学校帮他搬到新的教师公寓去了,老房子里的东西就都处理了。”
晓t梅给了我方教授新公寓的地址。
我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
谢过晓梅,我骑着车就往那个地址赶。
那是一个新建的家属小区,比我住的棚户区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我找到了那栋楼,却在楼下犹豫了。
我该怎么开口?
我这身收破烂的行头,保安会不会让我进?
就在我纠结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小区门口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在1992年,桑塔纳可是不折不扣的豪车,一般是单位领导的座驾。
但这辆车,没有挂单位的牌照,而且车窗玻璃贴着很深的膜,看不清里面。
一种本能的警惕,让我停下了脚步。
我躲在街角的一棵大树后面,盯着那辆车。
过了大致十几分钟,车门开了。
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从驾驶座上下来,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但眼神却很锐利,像鹰。
他没有进小区,而是在门口点了一根烟,一边抽,一边不时地朝小区里望。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这个人,我见过!
就在前几天,我在街上乱逛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当时我回头,就看到了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一闪而过。
就是他!
他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说……他也是为了那份文件来的?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炸开。
他们不是在找我。
他们是在找那个源头——方文博教授!
我瞬间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我刚才冒冒失失地找上门去,目前可能已经落到他们手里了。
我不敢再待下去,悄悄地推着车,离开了那个小区。
回出租屋的路上,我的脑子飞速运转。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这些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们既然能找到方教授,就必定能顺藤摸瓜,找到那个卖给我保险柜的收废品的小贩,然后找到我。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在他们找到我之前,联系上陆承远院士!
可是,怎么联系?
我再次陷入了绝境。
晚上,我躺在床上,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又捋了一遍。
文件,陆承远,方文博,戴眼镜的男人……
这些线索,像一团乱麻。
等等!
方文博!
他是物理系教授,陆承远是航空航天专家。
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他们是同事?是朋友?还是师生?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我需要更多关于方文博和陆承远的信息。
第二天,我又去了图书馆。
“晓梅,再帮我个忙。”
“又查什么?”晓梅看我神神秘秘的样子,有些好奇。
“帮我查查,江城大学物理系的方文博教授,还有……一个叫陆承远的人。”
“陆承远?哪个‘承’,哪个‘远’?”
“继承的承,远方的远。”
晓梅去查了。
这一次,花的时间更长。
直到中午,她才拿着几张手抄的纸条过来。
“方文博的资料好查,学校的名誉教授,这是他的履历。”
我接过来,快速地看着。
方文博,1925年生,早年留学苏联,是国内第一代核物理专家。
履历很辉煌,但我没看到任何和陆承远有关的字眼。
“那个陆承远呢?”我急切地问。
“这个难查。”晓梅摇摇头,“图书馆的公开资料里,根本没有这个人。我后来托大学图书馆的老师,在一些不对外开放的内部校史资料里,才找到一点线索。”
她把另一张纸条递给我。
“陆承远,好像也在江城大学待过,但时间很短,大致是五十年代末。他不是物理系的,好像是工程力学系的。后来,他的档案就被调走了,备注是……‘保密单位’。”
保密单位!
这个词,再次证实了我的猜想。
“还有别的吗?”
“还有,”晓梅说,“我在一份五十年代末的校刊上,找到了一张集体照,是当时学校青年教师的联谊活动。上面,好像同时有方文博和陆承远。”
“照片呢?”我激动地问。
“校刊不能外借,我也没法复印。我只能凭记忆画下来。”
晓梅拿出一支笔,在纸上画了两个草草的头像。
“这个是方文博,我见过他的照片,戴眼镜,头发有点秃。”
“这个,他旁边这个,应该就是陆承远。很年轻,很高,不戴眼镜,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我看着纸上那两个简笔画的头像,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如果他们是旧识,那么方教授必定知道怎么联系陆院士!
目前唯一的障碍,就是那个守在小区门口的眼镜男。
我必须想办法,避开他,见到方教授。
我需要一个帮手。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拐。
虽然他贪财,但他人不坏,而且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鬼点子多。
我回到废品站,把老拐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拐叔,帮我个忙。”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隐去了文件的具体内容,只说是很重大的东西),以及我的计划,都跟他说了。
老拐听完,半天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小进,你这是在玩火。”他最后说。
“我知道。”我看着他,“但目前没退路了。这火要是不灭,早晚把咱们都烧死。”
老拐看着我,眼神里有挣扎,有恐惧,但最后,他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用脚碾灭。
“妈的。”他骂了一句,“老子这辈子,还没干过这么刺激的事。说吧,要我怎么做?”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需要你帮我调虎离山。”
我的计划很简单。
我让老拐假扮成收煤气罐的,去小区里转悠,故意弄出点动静,把那个眼镜男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然后,我趁机从另一个方向溜进楼里,去找方教授。
第二天下午,我们按计划行动。
老拐蹬着他的破三轮,车上装着两个叮当作响的空煤气罐,嘴里喊着:“收煤气罐喽——旧煤气罐换钱——”
他故意在小区门口那辆桑塔纳旁边来回晃悠。
果然,那个眼镜男被他吵得不耐烦,从车上下来,皱着眉盯着他。
“喊什么喊!这里不准收废品!”
“我收煤气罐,又不是收废品。”老拐装出一副又横又愣的样子,“你管得着吗?”
“你……”眼镜男被噎了一下。
就在他们拉扯的时候,我猫着腰,从小区侧面的一个绿化带缺口,闪身溜了进去。
我心脏狂跳,一路小跑,找到了方教授住的那栋楼。
谢天谢地,楼门没锁。
我一口气跑到六楼,找到了602室。
我站在门口,做了几个深呼吸,才抬手敲了敲门。
咚,咚,咚。
敲门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响。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道缝。
一个满头白发、戴着老花镜的老人,从门缝里探出头来。
他看起来很虚弱,脸色苍白。
“你找谁?”
“请问……您是方文博教授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无害。
“我是。你是?”他警惕地看着我。
“我……我是一个收废品的。”我实话实说,“前几天,我从您家收了一批旧东西。”
方教授的眼神更警惕了。
“有什么事吗?”
“我在您卖的那个旧保险柜里,发现了一样东西。”我压低声音,“一样……很重大,不属于您的东西。”
方教授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猛地把门拉开。
“你进来!”
我跟着他走进屋里。
屋子很整洁,但充满了药味。
他把我带到客厅,关上门。
“你发现了什么?”他死死地盯着我,声音都在发抖。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怀里,掏出了那张晓梅画的简笔画。
“方教授,您认识这个人吗?”
方教授接过纸,扶了扶老花镜,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
他嘴唇哆嗦着,指着纸上那个笑起来有酒窝的年轻人。
“承远……陆承远……你……你怎么会有这个?”
我心里有底了。
“我发现的东西,就和陆承远院士有关。”
方教授的身体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我赶紧扶住他。
“您别激动。”
他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
“东西呢?东西在你身上吗?”
我点点头。
“快!快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
“教授,这东西太重大了。我必须确定,您能把它交到陆院士手里。”
方教授喘着粗气,他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孩子,你听我说。”他喝了口水,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
“那份文件,是承远几十年前,还在江城大学的时候,托我保管的。那时候,他被调去一个高度保密的单位,许多研究资料不能带走,又不能销毁,就藏在了我这里。”
“他为什么不自己收好?”
“他住的是集体宿舍,人多眼杂。我家有个保险柜,他说放我这最安全。后来……后来运动来了,大家自顾不暇,再后来,他就彻底没了音讯,我也联系不上他了。这一放,就是三十多年。”
“那您为什么把它卖了?”
方教授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我老了,糊涂了。前两年我老伴走了,我身体也垮了,记忆力越来越差。搬家的时候,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我……我把这事给忘了!我以为那是个空柜子,就当废铁处理了!”
他捶着自己的胸口,懊悔不已。
“我真是个罪人!我差点把国家的宝贝给弄丢了!”
“那目前怎么办?我怎么才能联系上陆院士?”
“我也不知道。”方教授一脸绝望,“他当年走的时候,只说去了北京,具体在哪个单位,我一概不知。我们已经三十多年没联系了。”
我的心,又沉到了谷底。
唯一的线索,断了。
就在这时,方教授突然想起了什么。
“等等!我想起来了!他当年走的时候,给我留过一个联系方式。他说,万一有天塌下来的事,就去北京找一个叫‘红星机械厂’的地方,找一个叫王铁柱的厂长。那是他的发小,最信得过的人。”
红星机械厂!王铁柱!
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好!我马上去北京!”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进。”
“陈进,好,好孩子。”方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这里面是我所有的积蓄,有两千块钱。你拿着,当路费。找到承远,告知他,我方文博对不起他,对不起国家!”
我推了回去。
“教授,这钱我不能要。”
“拿着!这是你应得的!”他强硬地塞给我,“你救了我的命,也救了这个国家!”
我正推辞着,突然,楼下传来一阵嘈杂声。
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正朝着楼上跑来。
我和方教授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恐。
“他们来了!”方教授脸色煞白。
“您快躲好!”我当机立断,把文件和钱都塞进怀里。
“你怎么办?”
“我自有办法!”
我冲到厨房,打开窗户。
这里是六楼,下面是草坪。
跳下去,不死也残。
但我看到,厨房窗户外,有一根粗大的下水管道,一直通到楼顶。
我没有丝毫犹豫,翻身爬了出去,像只壁虎一样,手脚并用,死死地抱住那根冰冷的管道。
几乎就在我爬出去的瞬间,房门被“砰”的一声撞开。
我听到了那个眼镜男的声音。
“方教授,我们没恶意,只是想请您配合一下。”
然后,是方教授虚弱而愤怒的声音。
“你们是什么人!滚出去!”
我不敢再听下去,咬着牙,拼命地往上爬。
我这辈子,从来没爬过这么高。
风在耳边呼啸,我的手心全是汗,好几次都差点滑下去。
等我终于爬上天台,整个人都虚脱了,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不敢停留,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不见了。
我从天台,跳到隔壁单元的楼顶,然后顺着楼梯,一路跑了下去。
跑到小区门口,我看到老拐还在跟保安纠缠。
我对他使了个眼色。
老拐心领神会,推着三轮车,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也混在人群里,迅速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
当晚,我没有回出租屋。
我知道那里已经不安全了。
我找到了老拐。
“拐叔,借我点钱,我要去北京。”
老拐二话不说,从他床底下那个铁盒子里,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皱巴巴的,一共三百多块。
“加上方教授给的两千,够了。”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老拐担忧地说。
“没办法。”我把那份文件,小心地贴身藏好,“这东西,只有我亲自送去才放心。”
临走前,我去了一趟图书馆。
隔着窗户,我看到晓梅正在灯下安静地看书。
我没有去打扰她。
我怕我一看到她,就走不了了。
我在心里对她说:等我回来。
然后,我转身,走进了夜色中。
我买了当天晚上去北京的绿皮火车票。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
车厢里拥挤不堪,充满了汗味、泡面味和各种奇怪的味道。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紧紧地抱着我的挎包,一夜都没敢合眼。
我感觉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像是那个眼镜男派来的。
火车咣当咣当,走了十几个小时,终于在第二天下午,抵达了北京站。
走出车站,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和高楼大厦,我有点发懵。
这就是北京。
我顾不上感叹,找人问了路,就直奔那个“红星机械厂”。
红星机械厂在南城,是个老国企。
我找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工厂大门紧闭,门口的牌子都生锈了。
我问了门卫,门卫大爷告知我,厂子早就不景气了,半停产状态。
“你找王铁柱厂长?”大爷打量着我,“他早就不是厂长了,退二线了。”
我的心又是一沉。
“那……那您知道他住哪吗?”
“你找他干嘛?”
“我是他一个老乡的晚辈,家里有急事找他。”我只能撒谎。
大爷看我一脸焦急,不像是坏人,就给我指了路。
“往里走,第三栋家属楼,二单元,401。”
我千恩万谢,跑进了家属区。
找到401,我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
他穿着一件旧背心,手里还拿着一把蒲扇。
“你找谁?”
“请问……您是王铁柱王叔叔吗?”
“我是。你是?”
“我……我是陆承远陆叔叔托我来的。”我直接报出了名字。
王铁柱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一把将我拉进屋里,反手就把门锁上了。
“你再说一遍?你找谁?”
“陆承远。”
“承远?他还好吗?他目前在哪?”王铁柱激动地抓住我的肩膀。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我就是来找您的,想通过您联系上他。”
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
王铁柱听完,脸色越来越凝重。
“好小子,有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承远没信错人。”
“王叔,您能联系上陆院士吗?”
王铁柱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没有他的直接联系方式。但是……”他走到电话旁边,“我有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当年留给我的,说只有天塌下来的时候才能打。”
他从一个上锁的抽屉里,翻出一个泛黄的本子。
本子最后一页,用钢笔写着一串数字。
没有区号,就是一个北京本地的号码。
王铁柱拿起电话,他的手也在抖。
他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
“喂,你找谁?”一个很严肃的声音。
“我找……我找首长。”王铁柱的声音有些干涩,“我是王铁柱,陆承远让我打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那个声音说:“在原地等着,不要动,不要跟任何人说话。”
说完,电话就挂了。
王铁柱长出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
“好了。”他说,“我们等着就行了。”
接下来的等待,是漫长而煎熬的。
大致过了一个小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不轻不重,很有节奏。
王铁柱过去开了门。
门口站着两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他们出示了一个红色的证件。
我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只看到了国徽。
“王铁柱同志,陈进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他们下楼。
楼下停着的,不是桑塔纳,而是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
上车后,车子一路疾驰,最后开进了一个我完全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
这里戒备森严,到处都是站岗的士兵。
我被带进了一间很简洁的办公室。
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气度不凡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
“你就是陈进?”他问。
我点点头。
“东西呢?”
我从怀里,掏出了那个油布包。
他接过去,小心地打开,拿出那份文件。
他只翻了几页,脸色就变得无比严肃。
“你做得很好。”他看着我,眼神里有赞许,“从目前开始,关于这件事,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一个字,包括你的家人朋友。清楚吗?”
“清楚。”
“你一路上,有没有被什么人跟踪?”
我想起了那个眼镜男。
“有。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开一辆黑色桑塔纳。”
“好,我们知道了。”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一个按钮。
“小李,带陈进同志去休憩。另外,通知行动组,可以收网了。”
我被带到一个招待所,吃了一顿这辈子都没吃过的丰盛晚餐。
然后,我睡了一个多月以来,最安稳的一觉。
第二天,我见到了陆承远院士。
他比我想象的要苍老一些,但精神很好,笑起来,真的有两个酒窝。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孩子,谢谢你。”他说,“你保护的,不仅仅是一份文件,而是我们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希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傻笑。
后来,我又被那个领导叫去谈话。
他告知我,那个眼镜男,是一个境外间谍组织的人。他们很早就盯上了这份资料,一直在想方设法地窃取。
方教授搬家,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幸好,文件阴差阳错地到了我手里。
“江城那边的人,已经全部抓获了。”领导说,“你立了大功。国家不会忘记你的。说吧,你有什么要求?”
我愣住了。
要求?
我想到了钱,想到了北京户口,想到了好工作。
但最后,我摇了摇头。
“我没什么要求。”
我说的是真心话。
在见到陆院士,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时候,我就已经满足了。
“不行。”领导笑了,“有功必赏。这样吧,你不是高考没考好吗?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不想重新上学?”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信任自己的耳朵。
“我……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他递给我一张纸,“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特招推荐信。你去那里,好好学习,将来,也来为国家做点事。”
我接过那张纸,手都在抖。
那张纸,比我见过的任何钱,任何宝贝,都重。
几天后,我坐上了回江城的火车。
来的时候,我是个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者。
回去的时候,我揣着一个全新的未来。
回到江城,我先去找了老拐。
我把那两千三百多块钱还给他。
“你小子,出息了。”老拐看着我,眼睛有点红,“后来就是国家干部了,可别忘了我这个收破烂的瘸子。”
“忘不了。”我给了他一个拥抱,“这辈子都忘不了。”
然后,我去了图书馆。
晓梅看到我,又惊又喜。
“你跑哪去了!急死我了!”她捶着我的胸口,眼泪都下来了。
我抓住她的手。
“晓梅,我过几天要去北京上学了。”
“上学?”她愣住了。
“嗯。”我把那封推荐信拿给她看。
她捂着嘴,眼里的泪,变成了喜悦的泪。
“你……你真的做到了。”
“晓梅,”我看着她,“等我。等我毕业,我就回来娶你。”
她哭着,笑着,用力地点头。
离开江城的那天,天气很好。
我最后去了一趟“前进废品回收站”。
老拐正蹲在磅秤边上,一口一口地嘬着他的“阿诗玛”。
阳光照在堆积如山的废品上,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
我突然觉得,这里也不是那么不堪。
每一件被人丢弃的旧物,都曾有过它的故事。
而我,也是从这堆“垃圾”里,捡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闪闪发光的未来。
我的人生,就像这辆永久牌二八大杠,曾经除了铃不响哪都响。
但从今天起,它终于要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叮当作响地,前进了。




![在苹果iPhone手机上编写ios越狱插件deb[超简单] - 鹿快](https://img.lukuai.com/blogimg/20251123/23f740f048644a198a64e73eeaa43e6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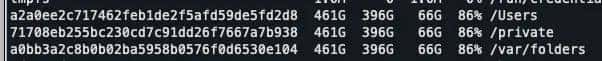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